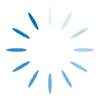宋也川僵硬着身子不敢动弹,生怕拉扯了她的伤处。
温昭明闭着眼睛,翘起的睫毛微微地颤。
她吻得不得章法,宋也川呼吸尽乱。
手上却又顾及着她的伤,不得不托着她的腰供她借力。
“殿下,吃饭……”霍逐风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宋也川猛地睁开眼,他回身看向已经空无一人的门口,脸顿时涨得通红。
“殿下。”他小声说,“霍侍卫必然在心里骂我。”
温昭明才醒,他便不知廉耻地与她纠缠,不知道阖府上下又该怎么看待他。
身后,温昭明吃吃地笑:“你就脸皮这么薄么?”
宋也川觑她:“好坏心的人,才醒来便要笑我。”
“譬如宫中,皇上御幸嫔妃,还有老太监在屋外听房。”温昭明脸色还苍白着,却已经开始和他说笑,“若你有这时候,岂不是羞死了。”
宋也川愣了一下,垂眸不看她:“皇家子嗣是国事……这不一样。”
他走至门口,端起台阶上的托盘,摸着还热:“是粥和青菜,吃不吃?”
“我要吃肉。”温昭明恹恹的,“不想吃这个。”
“要吃的。”宋也川不理会她的不满,“明天叫厨房做肉给你,今日只能吃这个。”
“那别的肉呢?”温昭明眼睛微微一转,“郎君身上的肉,能不能给我吃?”
宋也川撩开袖子,将自己的手臂送到她唇边:“吃么?”
温昭明果真不客气,张口便咬。
宋也川的手臂白皙,甚至可以看见青色的筋络和血管,温昭明咬在齿关之间,却又伸出舌尖,轻轻去舔。
宋也川只觉得脊背一阵麻意,忍不住嘶了一声。
温昭明得了兴味,又欲继续,宋也川舍不得说她,却又实在难忍:“停下。”
“你不喜欢这样吗?”她换了一种方式,继续在他手臂上作祟,“那这样呢?”
宋也川吸气:“不要闹了。”
窗边本有婢子经过的声音,听到屋里的动静,连脚步声都轻了,一溜烟就没了踪影。
“她们定是误会了。”宋也川低声说。
“那你去找她们坦白,说你根本和我无事发生?”温昭明终于舍得松开嘴,宋也川乌润的目光落在自己手臂上的齿痕上,心跳微乱。
“和殿下的时日久了,哪有人还会信我的清白。”宋也川小声啐她,“前阵子陛下说起其阳公主的亲事,有不少臣僚来向我打听……”
“打听什么?”
“打听如何谋得公主的欢心。”
温昭明忍笑忍得辛苦:“那你如何说?”
宋也川生硬道:“我说不知道。”
“然后呢?”
然后?宋也川面无表情:“你再不吃饭,粥就冷了。”
温昭明又去磨他:“郎君,你说嘛。你告诉我,我就把饭吃了。”
宋也川一手托碗一手拿汤匙,神色有些纠结。
“他说过去只觉得我行事不检,如今发现我不够坦诚,人品更差。”
温昭明终于笑出声来,她一手按着伤口,一手擦泪:“谁说的?”
“裴泓啊。”宋也川舀了一勺粥,“张口。”
温昭明张口含住汤匙:“他喜欢清影?”
宋也川对感情之事不太敏锐,含糊道:“也许吧。”
“那清影喜欢他吗?”
想到那天温清影看向池濯的目光,宋也川摇头:“好像不喜欢。”
“太有趣了。”温昭明兴致勃勃,“改天我去亲自问问。”
宋也川握着汤匙的手顿在半空,压低声音:“你给我留点情面,行不行?”
“到时候阖宫上下都要觉得我长舌。”宋也川将粥递到她唇边,“求殿下垂怜我。”
“这也不行,那也不好的。”温昭明将最后一勺粥吞下。
宋也川给她拿帕子擦手,再端了茶水漱口。
而后,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枚南珠。
这样的东西反倒是温昭明很谙熟,她扫了一眼便说:“这像是镶嵌在冠上的。”
宋也川嗯了一声:“那日抓到的人交代,有人给了他一张银票,我去了他所说的钱庄而后拿到了这张银票。上头盖的是信一堂的印章。我问过了信一堂的掌柜,他说是一个小厮模样的人,拿了这个珠子来典当。”
温昭明缓缓接过这个珠子:“这是南岛的荔珠。有头脸的士族也会买来当首饰,这么大的,十有八九是从宫里出去的。”
“若是买凶伤人,却没有现银,还要去典当。要么这珠子是偷来的,要么就是新贵乍富,才得脸的人物。”
温昭明有些疲倦地靠在引枕上:“他好大的胆子。”
她看向宋也川:“江尘述为何这般恨你?他不仅仅是要至你于死地,更是想让你受极刑而死。”
宋也川仍旧很平静:“平苏的盐课是在武帝时便敲定的数目,江尘述为了从中谋利,私自将其加入至田赋之中。这只是其一,还有更多拆东补西的例子,贪墨是重罪,尤其是以这种方式贪墨,不被律法所容,这些事一直都是我在管的。”
“没人弹劾他么?”
“有,但是不多,且下场都不大好。”宋也川不想让温昭明想太多,“你要不要睡会?”
温昭明点点头:“你呢?后来大理寺那边有没有再找你麻烦?”
“没有。”宋也川替温昭明将引枕取掉,“张淮序昨夜晚些时候来过一次,给我拿了一些卷宗来看,你一会睡觉,我坐这写东西陪你。”
听闻此言,温昭明言语之间不乏带有几分遗憾:“还以为你从此再也不用上朝了。”
她翻了个身:“你看吧,我睡了。”
宋也川今日看的是广惠库的卷宗。广惠库是皇城内的一处存银钱的库房,从各地运送至京城中的铜钱和宝钞都会在核定数额之后,统一交给广惠库保管。而白银则会交给户部。
去年因为先帝的丧仪和登极大典,户部和广惠库的现银各有损耗。皇帝自己的“内承运库”是维持宫廷的日常开支机构,里面的银子也去了半数。
所以温兖登基之后下令征收过一定比例的铜钱和宝钞以补充内库。总的征收额一定,户部的税银便因此大幅缩水。且新帝登基之后银钱耗费巨大,各地物料的供应也日渐紧缺,各部的钱粮都被挪用,放眼整个朝堂看去,许多漏洞已经初见端倪。
宋也川执笔写了两个时辰温昭明还没有睡醒。
于是他走出门,叫人将他才写好的东西送入宫去。
外头的奴才在议论着什么,宋也川问霍逐风:“他们在说什么?”
霍逐风压低了声音:“被圈禁在宫里的弘定公,昨夜过身了。连同他的世子,一并都没了。说是出了花,连夜拉出宫烧了。”
宋也川颔首:“和他们说,都不许议论了,若再有人乱说,拖出去发卖了。”
论名义,宋也川不是公主府的主子,可他的话所有人都会去听。霍逐风点头说是,他走起路来有些蹒跚,宋也川知道因为温昭明遇刺之事,他主动领了杖责。
“我这有药,你拿去用吧。”宋也川踅身,“等我一下。”
片刻后,他拿来一个瓶子:“这是我之前用过的,比一般跌打药效果好些。”
霍逐风忙谢过。
再走回内室时温昭明已经醒了,她的长发从榻上一直垂落到地衣上,她乌润的眼睛好似还没有完全醒来,看宋也川走过来,秀气地吸了吸鼻子:“你们外头在说什么?”
宋也川搬了个杌子在她身旁坐下:“弘定公过身了。”
温昭明沉默了一会,低声说:“温兖还是没有放过他。”
提起温襄,温昭明的心情依旧有些复杂。
他待她的情分余下多少温昭明不得而知,但与她而言,温襄始终是陪她长大的那个人。
她怨恨过他,也曾立誓不再与他往来,但听到这个消息,温昭明仍会觉得难过。
“他今年……三十一岁。”她低声说,“那我侄儿呢?”
宋也川沉默了,温昭明便明白了。
“也好。”她抬手擦去眼角的一滴泪,“死了比活着痛快些。”
*
温昭明的伤在肩膀上,沾不得水,平日里很多事都做起来费劲。
宋也川偶尔来搭把手,有时替她梳梳头。
他的巧手在这上面还是有些费力,梳了好几回才勉强学出个模样来。
日子难得过得平静了些,宋也川照常忙碌着,一直温襄尾七那一天,温昭明刚好进宫给温兖请安。
她的身体渐渐好转起来,只是人比过去还要畏寒些,入秋之后出门也更少了。
从三希堂出来时,她低声问冬禧:“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?”
“殿下指的是什么?”
“一种香味。”温昭明蹙着眉心,“但不好闻。”
“似乎有。”冬禧想了想,“殿下好端端的,怎么会问这个。”
温昭明缓缓摇头:“不知道,只是不喜欢这个气味。”
外面正在下雨,汉白玉石阶上积了一些水,空气带着一股湿淋淋的气味。冬禧为温昭明撑着伞,宫里头还在行走的奴才并不多。
“我记得,弘定公那阵子住在平园里。”
“殿下不会是想去吧,弘定公和世子是出了花没的,您身子还没好全,怎么能沾染这些……”
温昭明依稀地笑了一下:“你也信这话?没事的,咱们就当是路过,你叫我瞧一眼。”
过去,温昭明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慈悲的人,但随着年岁的增长,骤然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再会牵动她的心弦,可她却回忆起了一些人的好。
温襄不是好人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